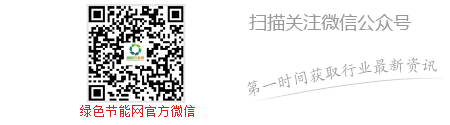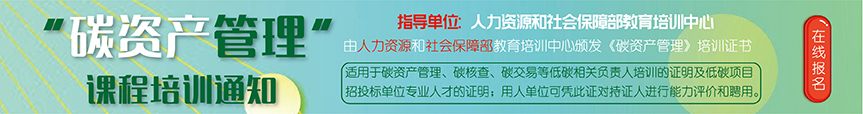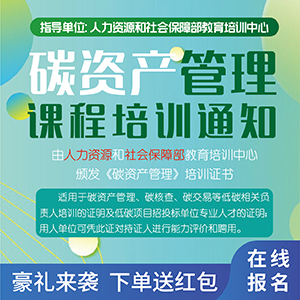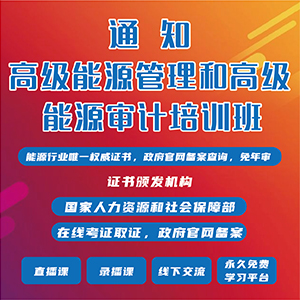[導讀]一個鳥類保護區,居然同時也是漁場。為了保護漁產,應該被保護的鳥兒們卻被人們轟走。

保護區監測記錄中,2008年還能見到的丹頂鶴、灰鶴,近兩年來都見不到了。

圖為貢格爾河上的攔魚壩
每遇鳥類遷徙和魚類繁殖的季節,生活在達里諾爾湖周邊的牧民常看到被炮聲驚飛的鳥群。今年春天,“雖然沒有聽到炮聲,但鳥類保護和魚鳥食物鏈的情況沒有任何改觀。” 剛從達里諾爾湖考察回來的達爾問自然求知社考察員常青告訴中外對話。
肩負著保護100多種從天鵝、白枕鶴到大鴇等過境野生鳥類的達里諾爾自然保護區,與國營漁場組成“一套班子,兩塊牌子”的連體雙生式管理單位。但是,為了保護漁產,贏得更多的經濟利益,保護區建立攔魚水壩,驅趕捕魚鳥類。達里諾爾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像中國許多自然保護區一樣,深陷于保護責任與經濟利益的矛盾之中。
“達里諾爾”蒙語意為“浩瀚的湖”,位于內蒙古克什克騰旗富饒的西部草原上,是中國北方候鳥遷徙路上重要的經停暫歇地。由于這樣重要的生態地位,達里諾爾在1986年建立了旗縣級自然保護區,1995年至1997年,連續升級至國家級自然保護區。
每逢4-5月,北遷的候鳥會途經達里諾爾,在湖邊的濕地草原休息、覓食。此時正是湖中主要魚類華子魚(瓦氏雅羅魚Leuciscus waleckii)繁殖季節,成千上萬的魚會離開堿性較高的達來諾爾,尋找淡水環境產卵。它們通常會選擇貢格爾河。這條發源自大興安嶺南端的河流在草原上蜿蜒百余公里之后,注入達里諾爾。華子魚沿著河道溯游而上,最遠能夠上游到距達里諾爾入湖口直線距離超過100公里的地方。
牧民寶音說,每到這個時節,河里就會擠滿了魚。河面上翻騰的魚有時甚至會跳到河岸上來。產卵的魚吸引著以捕魚為生的鳥類。蒼鷺最喜歡等在岸邊,專吃跳上岸的華子魚,當地牧民因此給它一個俗名叫“長脖老等”。滿河的魚成為遷徙途中食魚鳥類補充體能的美食。在春季的河灘草原上,成群飛落的鳥與安靜的畜群相伴,形成和諧美好的圖景。當地牧民寶音告訴我們,小時候如果弄死了魚或鳥,是會挨打的。從古至今,魚和鳥受到牧民傳統文化的保護。
上世紀五十年代,達里諾爾湖成立了國營達來諾日漁場,每年冬季開展大規模的冬捕。達里諾爾豐富的漁產成為物質貧乏時期重要的食物補充。
漁場建立之后,貢格爾河在七十年代建立了攔魚壩。華子魚溯游產卵的通路被阻斷了,僅剩下短短十幾公里的一條水量有限的河道。更多的華子魚則被迫選擇東邊連接崗更諾爾(淡水)湖的十多公里的沙里河溯游產卵。保護區的工作人員解釋,建立攔魚壩是為了保護魚產,減少因為河水流動造成的魚卵損失。也有調查者認為,攔河壩縮短了洄游路線,讓魚盡可能留在湖底,而不會進入河道太遠的地方。究其根本都是為了保護漁產。但漁產是不是真的被保護了?達里諾爾保護區水質監測數據顯示,湖水鹽堿度正在持續增加,已經接近魚類承受的臨界值,攔魚壩與不斷增加的鹽堿度有莫大的關系。對于淡水產卵的華子魚來說,更是生存與繁衍的雙重威脅。
由于食物和捕食范圍的減少,鳥類生存也面臨同樣的威脅。家住貢格爾河上游的牧民寶音回憶,自從貢格爾河修了攔魚壩之后,河里沒有魚了,以前在河邊出沒的一種吃魚的鳥,牧民叫它jahlai,現在也見不到了。常年觀測達里湖鳥類的常青介紹,近年來,依賴捕魚為生的鳥類被迫減少了活動和棲息的范圍。捕魚的鳥都集中到達里諾爾附近的沙里河邊。那里正是牧民發現鳥被炮轟的地方。常青告訴中外對話,在鳥類遷徙的季節,他也見過沙里河邊為驅鳥搭建的臨時帳篷,看到過工作人員用放炮的辦法驅散捕魚的鳥群。
現在,華子魚以其鮮美的肉質漸漸遠近聞名,僅在赤峰地區就已供不應求。工作人員介紹,近年購買華子魚已經需要提前預定了,市場上都很難買到,市面價格已經漲到了30元/斤。然而華子魚的數量卻在持續減少,近年捕獲的華子魚越來越小。為了保證效益,漁場還開發了人工繁殖技術,以彌補華子魚自然產卵的不足。
一方面漁場在努力保護漁產,但另一方面漁產和鳥類卻都在減少。自攔魚壩建立之后,食魚候鳥的活動區域被限制在漁場和保護區管控的方圓二十幾公里范圍之內。在候鳥過境季節,在工作人員的驅趕之下,出現在達里諾爾地區的鳥減少了。保護區管理人員也承認:“這兩年,本地鳥類的數量應該說是下降了,鳥的種類也在減少。”保護區監測記錄中,2008年還能見到的丹頂鶴、灰鶴,近兩年來都見不到了。
在達里諾爾湖北岸的事業單位門前,“克什克騰旗達來諾爾漁場”和“國家級達里諾爾自然保護區管理處”兩個牌子并排掛在大門口。1997年以后,達里諾爾保護區按照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的規定,設立了自然保護區管理處,管理處主任由達來諾日漁場場長兼任。用保護區工作人員的話說,這是“一套班子,兩個單位”。保護區在漁場的基礎上建立,其內部許多工作人員是由漁場的職工兼任的,少部分自然保護專業人員為外招。這樣形成了一個工作團隊兩個單位,兼顧保護和漁業生產的管理模式。同樣的情況在中國保護區中比比皆是,達里諾爾保護區工作人員介紹,克什克騰旗的白音敖包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主任也是由白音敖包林場場長兼任的。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國人與生物圈國家委員會成員告訴中外對話,中國的大多數自然保護區是采取就地保護的方式,在原先的林場、漁場等國有企業地盤上建立起來的。在自然保護工作中,國有企業卻成為一個尷尬的歷史遺留問題,使經濟效益與自然保護矛盾造成的陰影長期困擾著自然保護區。
他介紹,漁場原有班子在經過整合吸納自然保護技術人員之后,形成兩個單位的復雜機構。國家給自然保護區的優先撥款卻僅夠養活保護區編制內的員工,這在利益分配過程中常常形成內部矛盾。而漁場原有的龐大編制則成為沉重的經濟壓力,往往是國有企業不顧自然保護,追求經濟效益的難言之隱。這種壓力是保護區內各種經濟開發的原始動力,旅游、種植、養魚是常見的產業。
今年四月底,又一個魚類產卵、鳥類遷徙的季節里,華子魚仍然像往年一樣聚集在欄魚壩下,盼望著洄游,過境的鳥兒盤旋在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