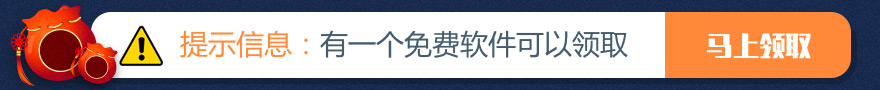有人說,“油荒電荒”年年有,今年似乎特別多。
環顧四周,突然走進我們生活的“電荒”不禁讓人聯想起剛過去的“油荒”。繼“石化雙雄”煉油廠巨虧之后,電力央企又巨虧了。縱觀中國經濟,許多人都產生了這樣一個疑問:為什么“巨虧”的總是你們?
今冬,電荒來襲!
據上海證劵報報道,電力企業正面臨著2008年以來最為嚴峻的運營壓力,局部地區電荒苗頭再現,部分省市或再次面臨拉閘限電考驗。電力緊張也成為鋼貿企業關注的焦點。
今冬明春將面臨電荒
電監會發布的《全國電力供需及電煤供應檢測預警信息》顯示,截至10月下旬,全國日缺煤停機容量最大達到近1600萬千瓦,云南、貴州、四川、湖南、重慶等省市發電企業電煤庫存平均可用天數已下降至警戒線7天以下。
電監會預測,位于華中地區的湖北、湖南、江西、河南、安徽、重慶等六個省市今冬明春的電力缺口將達到1500千瓦,為歷年來最大,而湖南、湖北、廣西、貴州、蘭州等17個省市,面臨著新一輪拉閘限電的可能。
業內人士指出,在通脹壓力有所緩解的背景下,電價近期在全國范圍內上調的必要性、可能性正進一步加大。同時,明年1月1日開始實施的火電廠排放新標準,也增加了上調電價的緊迫性。
據了解,歷次“電荒”的影響總是鋼鐵行業首當其沖,因鋼鐵大致占全部用電需求的12.7%,屬于電力的最大消耗行業。每次如果出現電力緊張,鋼鐵便首當其沖成為限制電力的目標。因此分析人士指出,今冬或難避免拉閘限電,這也成為鋼貿企業所關注的話題。
“巨虧”又見“巨虧” 國資委調研電企
據中國證券報報道,電力企業正面臨著2008年以來最為嚴峻的運營壓力,局部地區電荒苗頭再現,部分省市或再次面臨拉閘限電考驗。在通脹壓力有所緩解的背景下,電價近期在全國范圍內上調的必要性、可能性正進一步加大。
該報道稱,有關部門近期已將電價調價方案上報。考慮到通脹下降趨勢已經確立,電價調價方案近期獲批的可能性較大。
不過,據《證券市場周刊》報道,發改委價格司有關負責人表示,并沒有看到調價方案。
據21世紀經濟報道稱,發改委能源研究所一位專家分析,電價上調何時出臺,上調多少還要由國務院依照形勢來定奪,現在CPI剛有穩定趨勢,如果下月能繼續穩定住,才可能有機會。
雖然目前尚無電價上調方案的確切消息,但電價上調何時出臺卻牽動人心。特別是隨著從電力企業三季報的出爐,電價上調預期也漸漸走強。
電力企業虧損如何?
據21世紀經濟報道稱,電企人士透露,最近國資委已經派出工作組就電力央企巨虧問題調研。而中電聯對五大發電集團今年1-7月的經營情況統計顯示,五大集團合計虧損74.6億。
另據每日經濟新聞報道,從電力企業三季報可以看出,前三季度電力板塊利潤額同比下滑逾26%。另外,該報記者從業界獲悉,在脫硝電價尚未出臺的情況下,電力企業很難在已經嚴重虧損的情況下承擔如此大的運行成本。如不及時上調電價,已經虧損嚴重的電力企業將更加缺乏發電積極性。
今年4月10日,發改委上調了12個省份上網電價,上調幅度在2分/千瓦時左右。6月1日,發改委又上調15個省市工商業、農業用電價格。
業界人士指出,考慮到電力企業的虧損是全國范圍的,因此調價范圍可能不再限于局部。
電價上調迫在眉睫?官方尚未表態
據財訊網報道,短期之內全國電價或上調,幅度為2分/度左右,今年4月10日,發改委上調了12個省份上網電價。6月1日,發改委又上調15個省市工商業、農業用電價格。而此次電價調整將是全國性的電價上調。分析認為,CPI連續三個月回落,為電價調整創造了條件。此次電價上調之后,對通脹的負面影響還有待觀察。
有學者分析認為,虧損嚴重的電力企業缺乏發電積極性。電力缺口不斷擴大,上調電價比較現實,電價上調只是時間問題。事實上電力企業虧損已經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了,據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透露,電力行業05年全年的虧損面達到了27%。
而最新數據顯示,今年的7月份,華能、大唐、華電、國電、中電投五大發電集團電力業務合計虧損擴大,達9.8億元,比6月增虧1.8億元,上年同期盈利22.6億元。其中,電力業務中,火電虧損的情況正在加劇。4-7月份各月,火電業務分別虧損17.1億、16.9億、29.0億和28.5億元,月度虧損額擴大。火電在我國電力結構中的比例超過70%,一旦火電板塊出現問題,將會進一步加劇電荒現象。除此之外,受到緊縮貨幣政策的影響,電力企業財務費用大增值得關注,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電力行業的利息支出達到766億元,超過同期電力行業實現的利潤總額。
上調電價的背后:火電廠將誕生“最賠錢央企” ?
據新聞網報報道,攀至最高的煤價、降到冰點的庫存、數十家瀕臨破產的發電廠……近日種種跡象表明,旺季在即,一場“電荒”將在所難免。出乎意料的是,今年的勢頭似乎盛況空前。
據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預測,華中地區的湖北、湖南、江西、河南、安徽、重慶六省市今冬明春的電力缺口都將達到1500萬千瓦左右,均為歷年來最大缺口。記者注意到,目前部分電企煤炭庫存量已遠遠突破15天的監管要求,有些甚至只有3天。
缺電,這一季節性“綁架”眾多工業企業的“罪魁”,在入冬之際又站到了臺前。而接踵而來的古老命題仍然是:究竟誰該為一年數度的“電荒”負責?
火電廠現狀:將誕生最賠錢央企
昨日,一個消息不脛而走:大唐集團旗下30家電廠資產負債率已超過100%,嚴重資不抵債;其余也徘徊在80%-90%的非正常水平,超過了火電行業70%的正常負債率水平。若不是依靠銀行信貸苦苦支撐,曾經的央企“巨無霸”已到了“關門歇業”的邊緣。目前火電廠平均煤炭庫存只夠5、6天的發電需要,不僅遠遠低于15天的正常庫存,也低于7天的最低警戒線。虧損面高達67%的大唐集團年內已虧損30多億元,全年預計超過40億元,很可能成為“最賠錢”央企。而華能、國電、華電、中電投等另四大發電集團也都深陷虧損泥沼。有業內估算稱,近三年火電全行業虧損破千億元。
聲音:都是“夾板氣”惹的禍!
“從產能看不可能缺電,現在機器比以前好了,利用小時卻不高,因為許多電廠自覺關停了部分機組。”華能國際一位人士對記者坦言,這樣才能避免越生產越虧損的惡性循環,“我們購買的煤價是市場化地水漲船高,賣給電網公司的上網電價卻受政策管控,電廠完全受高煤價的鉗制。”
記者注意到,2009年以后,秦皇島動力煤價格漲至1000元/噸的歷史高位,煤炭市場已徹底變為賣家市場,結算方式也從以前的“先運煤,發電后付款”變為了“先付款,再運煤發電。”
由于多數火電廠資金鏈緊張,不得不違約拖延付款,后一種付款方式相當于變相漲價。
記者從國家電網能源研究所拿到的一份報告分析顯示,2008年電力行業虧損額達到850億元,負債率也快速上升,而同年,全國規模以上煤炭企業實現利潤2100億元,煤電矛盾已白熱化。
煤企現狀:超過90%前三季賺錢
與電廠的蕭條直接對抗的,是煤炭上市公司的靚麗業績。根據中央財經大學中國煤炭經濟研究院煤炭上市公司研究中心統計,今年前三季度39家煤炭行業上市公司利潤總額1103億,同比增長17.5%;0.64元的平均每股收益比滬深兩市全部上市公司平均數值高出了整整一倍。
作為中國煤炭市場的風向標,環渤海動力煤價格已連續三周維持在指數發布以來的歷史高位。秦皇島海運煤炭網指數中心9日數據顯示:5500大卡動力煤綜合平均價格為853元/噸,已經打破該指數運行一年多來的最高水平。此前,該價格指數連續四期保持上漲,整體上漲24元/噸。與同期相比,上漲了70元/噸。由于煤炭資源緊張,湖北、湖南、山東等省的煤炭用戶則不得不開通船煤航線,從秦皇島等港口采購煤炭。以湖北恩施地區為例,發熱量為5500大卡半煙煤10月連續2次上漲,整體漲幅達50元/噸,現坑口全票價格高達750元/噸。
聲音:職工收入水平最低!
昨日,一位從事煤炭行業十數年的資深人士回應記者,“電力行業職工人均收入要比煤炭行業高4-5倍,他們所說的虧損依據的成本信息有沒有可能失真?”
記者翻閱年報發現,以華電國際為例,截止2010年末,公司共有員工21283人,比2009年末增添了3225人,但在“合并現金流量表”中可以看到,“支出給職工及為職工支出的現金”較上年增添了3.21億元。這相當于2009年人均“到手”工資約10萬元,2010年還略有增添。而這還只是指公司現實支出的現金,對于公司已經計提但沒有支出的工資、獎金等,表此刻資產欠債表“應付職工薪酬”科目,2010年這項數額共增添了21.31億元。
華能國際情況也近似,該公司2010年在人員工33811人,僅比2009年末增添224人,“支出給職工及為職工支出工資、社會保險及教育經費等現金”科目卻顯示,增添了4.26億元。剔除員工增添身分外考量,四大發電集體往年末支出給職工的薪酬均不降反升。此外,由于下游能源“富翁”國家電網和南方電網并未直接上市,兩大供電集團的高管及職工收入依然諱莫如深。煤炭人士強調,煤炭本身是不可再生能源,過去估值偏低,實行"市場煤"機制之后,價格是回歸到了正常水平。
環顧四周,突然走進我們生活的“電荒”不禁讓人聯想起剛過去的“油荒”。繼“石化雙雄”煉油廠巨虧之后,電力央企又巨虧了。縱觀中國經濟,許多人都產生了這樣一個疑問:為什么“巨虧”的總是你們?
今冬,電荒來襲!
據上海證劵報報道,電力企業正面臨著2008年以來最為嚴峻的運營壓力,局部地區電荒苗頭再現,部分省市或再次面臨拉閘限電考驗。電力緊張也成為鋼貿企業關注的焦點。
今冬明春將面臨電荒
電監會發布的《全國電力供需及電煤供應檢測預警信息》顯示,截至10月下旬,全國日缺煤停機容量最大達到近1600萬千瓦,云南、貴州、四川、湖南、重慶等省市發電企業電煤庫存平均可用天數已下降至警戒線7天以下。
電監會預測,位于華中地區的湖北、湖南、江西、河南、安徽、重慶等六個省市今冬明春的電力缺口將達到1500千瓦,為歷年來最大,而湖南、湖北、廣西、貴州、蘭州等17個省市,面臨著新一輪拉閘限電的可能。
業內人士指出,在通脹壓力有所緩解的背景下,電價近期在全國范圍內上調的必要性、可能性正進一步加大。同時,明年1月1日開始實施的火電廠排放新標準,也增加了上調電價的緊迫性。
據了解,歷次“電荒”的影響總是鋼鐵行業首當其沖,因鋼鐵大致占全部用電需求的12.7%,屬于電力的最大消耗行業。每次如果出現電力緊張,鋼鐵便首當其沖成為限制電力的目標。因此分析人士指出,今冬或難避免拉閘限電,這也成為鋼貿企業所關注的話題。
“巨虧”又見“巨虧” 國資委調研電企
據中國證券報報道,電力企業正面臨著2008年以來最為嚴峻的運營壓力,局部地區電荒苗頭再現,部分省市或再次面臨拉閘限電考驗。在通脹壓力有所緩解的背景下,電價近期在全國范圍內上調的必要性、可能性正進一步加大。
該報道稱,有關部門近期已將電價調價方案上報。考慮到通脹下降趨勢已經確立,電價調價方案近期獲批的可能性較大。
不過,據《證券市場周刊》報道,發改委價格司有關負責人表示,并沒有看到調價方案。
據21世紀經濟報道稱,發改委能源研究所一位專家分析,電價上調何時出臺,上調多少還要由國務院依照形勢來定奪,現在CPI剛有穩定趨勢,如果下月能繼續穩定住,才可能有機會。
雖然目前尚無電價上調方案的確切消息,但電價上調何時出臺卻牽動人心。特別是隨著從電力企業三季報的出爐,電價上調預期也漸漸走強。
電力企業虧損如何?
據21世紀經濟報道稱,電企人士透露,最近國資委已經派出工作組就電力央企巨虧問題調研。而中電聯對五大發電集團今年1-7月的經營情況統計顯示,五大集團合計虧損74.6億。
另據每日經濟新聞報道,從電力企業三季報可以看出,前三季度電力板塊利潤額同比下滑逾26%。另外,該報記者從業界獲悉,在脫硝電價尚未出臺的情況下,電力企業很難在已經嚴重虧損的情況下承擔如此大的運行成本。如不及時上調電價,已經虧損嚴重的電力企業將更加缺乏發電積極性。
今年4月10日,發改委上調了12個省份上網電價,上調幅度在2分/千瓦時左右。6月1日,發改委又上調15個省市工商業、農業用電價格。
業界人士指出,考慮到電力企業的虧損是全國范圍的,因此調價范圍可能不再限于局部。
電價上調迫在眉睫?官方尚未表態
據財訊網報道,短期之內全國電價或上調,幅度為2分/度左右,今年4月10日,發改委上調了12個省份上網電價。6月1日,發改委又上調15個省市工商業、農業用電價格。而此次電價調整將是全國性的電價上調。分析認為,CPI連續三個月回落,為電價調整創造了條件。此次電價上調之后,對通脹的負面影響還有待觀察。
有學者分析認為,虧損嚴重的電力企業缺乏發電積極性。電力缺口不斷擴大,上調電價比較現實,電價上調只是時間問題。事實上電力企業虧損已經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了,據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透露,電力行業05年全年的虧損面達到了27%。
而最新數據顯示,今年的7月份,華能、大唐、華電、國電、中電投五大發電集團電力業務合計虧損擴大,達9.8億元,比6月增虧1.8億元,上年同期盈利22.6億元。其中,電力業務中,火電虧損的情況正在加劇。4-7月份各月,火電業務分別虧損17.1億、16.9億、29.0億和28.5億元,月度虧損額擴大。火電在我國電力結構中的比例超過70%,一旦火電板塊出現問題,將會進一步加劇電荒現象。除此之外,受到緊縮貨幣政策的影響,電力企業財務費用大增值得關注,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電力行業的利息支出達到766億元,超過同期電力行業實現的利潤總額。
上調電價的背后:火電廠將誕生“最賠錢央企” ?
據新聞網報報道,攀至最高的煤價、降到冰點的庫存、數十家瀕臨破產的發電廠……近日種種跡象表明,旺季在即,一場“電荒”將在所難免。出乎意料的是,今年的勢頭似乎盛況空前。
據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預測,華中地區的湖北、湖南、江西、河南、安徽、重慶六省市今冬明春的電力缺口都將達到1500萬千瓦左右,均為歷年來最大缺口。記者注意到,目前部分電企煤炭庫存量已遠遠突破15天的監管要求,有些甚至只有3天。
缺電,這一季節性“綁架”眾多工業企業的“罪魁”,在入冬之際又站到了臺前。而接踵而來的古老命題仍然是:究竟誰該為一年數度的“電荒”負責?
火電廠現狀:將誕生最賠錢央企
昨日,一個消息不脛而走:大唐集團旗下30家電廠資產負債率已超過100%,嚴重資不抵債;其余也徘徊在80%-90%的非正常水平,超過了火電行業70%的正常負債率水平。若不是依靠銀行信貸苦苦支撐,曾經的央企“巨無霸”已到了“關門歇業”的邊緣。目前火電廠平均煤炭庫存只夠5、6天的發電需要,不僅遠遠低于15天的正常庫存,也低于7天的最低警戒線。虧損面高達67%的大唐集團年內已虧損30多億元,全年預計超過40億元,很可能成為“最賠錢”央企。而華能、國電、華電、中電投等另四大發電集團也都深陷虧損泥沼。有業內估算稱,近三年火電全行業虧損破千億元。
聲音:都是“夾板氣”惹的禍!
“從產能看不可能缺電,現在機器比以前好了,利用小時卻不高,因為許多電廠自覺關停了部分機組。”華能國際一位人士對記者坦言,這樣才能避免越生產越虧損的惡性循環,“我們購買的煤價是市場化地水漲船高,賣給電網公司的上網電價卻受政策管控,電廠完全受高煤價的鉗制。”
記者注意到,2009年以后,秦皇島動力煤價格漲至1000元/噸的歷史高位,煤炭市場已徹底變為賣家市場,結算方式也從以前的“先運煤,發電后付款”變為了“先付款,再運煤發電。”
由于多數火電廠資金鏈緊張,不得不違約拖延付款,后一種付款方式相當于變相漲價。
記者從國家電網能源研究所拿到的一份報告分析顯示,2008年電力行業虧損額達到850億元,負債率也快速上升,而同年,全國規模以上煤炭企業實現利潤2100億元,煤電矛盾已白熱化。
煤企現狀:超過90%前三季賺錢
與電廠的蕭條直接對抗的,是煤炭上市公司的靚麗業績。根據中央財經大學中國煤炭經濟研究院煤炭上市公司研究中心統計,今年前三季度39家煤炭行業上市公司利潤總額1103億,同比增長17.5%;0.64元的平均每股收益比滬深兩市全部上市公司平均數值高出了整整一倍。
作為中國煤炭市場的風向標,環渤海動力煤價格已連續三周維持在指數發布以來的歷史高位。秦皇島海運煤炭網指數中心9日數據顯示:5500大卡動力煤綜合平均價格為853元/噸,已經打破該指數運行一年多來的最高水平。此前,該價格指數連續四期保持上漲,整體上漲24元/噸。與同期相比,上漲了70元/噸。由于煤炭資源緊張,湖北、湖南、山東等省的煤炭用戶則不得不開通船煤航線,從秦皇島等港口采購煤炭。以湖北恩施地區為例,發熱量為5500大卡半煙煤10月連續2次上漲,整體漲幅達50元/噸,現坑口全票價格高達750元/噸。
聲音:職工收入水平最低!
昨日,一位從事煤炭行業十數年的資深人士回應記者,“電力行業職工人均收入要比煤炭行業高4-5倍,他們所說的虧損依據的成本信息有沒有可能失真?”
記者翻閱年報發現,以華電國際為例,截止2010年末,公司共有員工21283人,比2009年末增添了3225人,但在“合并現金流量表”中可以看到,“支出給職工及為職工支出的現金”較上年增添了3.21億元。這相當于2009年人均“到手”工資約10萬元,2010年還略有增添。而這還只是指公司現實支出的現金,對于公司已經計提但沒有支出的工資、獎金等,表此刻資產欠債表“應付職工薪酬”科目,2010年這項數額共增添了21.31億元。
華能國際情況也近似,該公司2010年在人員工33811人,僅比2009年末增添224人,“支出給職工及為職工支出工資、社會保險及教育經費等現金”科目卻顯示,增添了4.26億元。剔除員工增添身分外考量,四大發電集體往年末支出給職工的薪酬均不降反升。此外,由于下游能源“富翁”國家電網和南方電網并未直接上市,兩大供電集團的高管及職工收入依然諱莫如深。煤炭人士強調,煤炭本身是不可再生能源,過去估值偏低,實行"市場煤"機制之后,價格是回歸到了正常水平。
電網公司現狀:切走65%行業營收
過去一直環繞于“煤電頂牛”的種種非議,隨著電企哭窮和煤企抱屈,漸漸向下游轉移。去年的一組官方數據更讓市場將火力對準了電網公司:來自國家統計局公告顯示,2010年前11個月,電網實現營業收入2.19萬億元,占整個電力行業的65%;利潤總額達到592億元,同比暴增1828%,行業占比42%。
電網暴富是否該為電荒負責?據記者了解,長期以來,電網輸配電成本核算和支出一直是電網企業最神秘的領地之一,成本含糊也令利潤空間曖昧不清。
國務院政策研究室副司長范必曾對媒體表示,電網輸配電的合理成本構成一般包括技術成本、人員工資、管理成本等,但電網實際核算過程中,說不清的交叉補貼和銷售環節各種形式的收費也附加其中,這些附加成本最終都反映到了配電側終端的銷售電價上,導致上網電價與銷售電價之間的價差過大,電網企業成本加利潤構成存在一定的“灰色空間”。
聲音:不存在暴利之說!
對于公眾質疑,國家電網副總經理舒印彪曾明確回應稱,國家電網有2萬億的資產,400億的利潤并不高,電荒主要由電力供求關系緊張引起,和電網的利潤沒有關系,不存在讓利的問題。
但如此回應卻難堵悠悠之口。由于成本信息極不透明,對輸配成本的監管缺少令人信服的依據。國家電監會資料顯示,去年國內電網企業平均輸配電價不含線損)為160.91元/千千瓦時,占銷售電價的28.15%。
以甘肅送華中交易(主要輸電通道為德寶直流)為例,2010年在交易過程中,甘肅省電力公司按30元/千千瓦時收取輸電費,陜西省電力公司收取1.45%的網損,西北電網公司按24元/千千瓦時收取輸電費,國家電網公司按46元/千千瓦時收取輸電費并收取5.31%的網損,華中電網公司按24元/千千瓦時收取輸電費,五家電網企業輸電價格合計達到124元/千千瓦時。如果包含德寶容量電費分攤和各環節網損,整個交易中間成本高達160元/千千瓦時。
結語:種種困境之下,電價上調是不是企業擺脫困境的惟一出路?
目前,我國多數電力企業目前還是屬于高耗能低產出,不少電力企業的單位電度產品的煤炭消耗遠遠超過400克,有的甚至超過500克,超出國外同類電力企業耗能的20%以上。如何降低成本是電力企業首先應該解決的問題,其次,此為電力企業員工高福利待遇,也被質疑是導致虧損的主要原因。
企業虧損不能簡單的將原因歸結于外部原因。國有企業高福利,低效率的問題飽受指責,解決這一問題需要打破行業壟斷,實現合理競爭。讓電力企業產生危機意識,是解決電企困境的另外一條途徑。
加強內部建設的同時,對于煤炭企業也不能聽之任之,應該加大對煤炭企業的資源稅征收力度,采取計資源稅價征收的方法,這樣有利于遏制煤炭企業的暴利,用這部分錢貼補電力企業,以此來平衡整個產業的利益分配格局。
過去一直環繞于“煤電頂牛”的種種非議,隨著電企哭窮和煤企抱屈,漸漸向下游轉移。去年的一組官方數據更讓市場將火力對準了電網公司:來自國家統計局公告顯示,2010年前11個月,電網實現營業收入2.19萬億元,占整個電力行業的65%;利潤總額達到592億元,同比暴增1828%,行業占比42%。
電網暴富是否該為電荒負責?據記者了解,長期以來,電網輸配電成本核算和支出一直是電網企業最神秘的領地之一,成本含糊也令利潤空間曖昧不清。
國務院政策研究室副司長范必曾對媒體表示,電網輸配電的合理成本構成一般包括技術成本、人員工資、管理成本等,但電網實際核算過程中,說不清的交叉補貼和銷售環節各種形式的收費也附加其中,這些附加成本最終都反映到了配電側終端的銷售電價上,導致上網電價與銷售電價之間的價差過大,電網企業成本加利潤構成存在一定的“灰色空間”。
聲音:不存在暴利之說!
對于公眾質疑,國家電網副總經理舒印彪曾明確回應稱,國家電網有2萬億的資產,400億的利潤并不高,電荒主要由電力供求關系緊張引起,和電網的利潤沒有關系,不存在讓利的問題。
但如此回應卻難堵悠悠之口。由于成本信息極不透明,對輸配成本的監管缺少令人信服的依據。國家電監會資料顯示,去年國內電網企業平均輸配電價不含線損)為160.91元/千千瓦時,占銷售電價的28.15%。
以甘肅送華中交易(主要輸電通道為德寶直流)為例,2010年在交易過程中,甘肅省電力公司按30元/千千瓦時收取輸電費,陜西省電力公司收取1.45%的網損,西北電網公司按24元/千千瓦時收取輸電費,國家電網公司按46元/千千瓦時收取輸電費并收取5.31%的網損,華中電網公司按24元/千千瓦時收取輸電費,五家電網企業輸電價格合計達到124元/千千瓦時。如果包含德寶容量電費分攤和各環節網損,整個交易中間成本高達160元/千千瓦時。
結語:種種困境之下,電價上調是不是企業擺脫困境的惟一出路?
目前,我國多數電力企業目前還是屬于高耗能低產出,不少電力企業的單位電度產品的煤炭消耗遠遠超過400克,有的甚至超過500克,超出國外同類電力企業耗能的20%以上。如何降低成本是電力企業首先應該解決的問題,其次,此為電力企業員工高福利待遇,也被質疑是導致虧損的主要原因。
企業虧損不能簡單的將原因歸結于外部原因。國有企業高福利,低效率的問題飽受指責,解決這一問題需要打破行業壟斷,實現合理競爭。讓電力企業產生危機意識,是解決電企困境的另外一條途徑。
加強內部建設的同時,對于煤炭企業也不能聽之任之,應該加大對煤炭企業的資源稅征收力度,采取計資源稅價征收的方法,這樣有利于遏制煤炭企業的暴利,用這部分錢貼補電力企業,以此來平衡整個產業的利益分配格局。
國家實施電力體制改革,的目的是為了實現行業的良性發展,從而最終逐步推進形成市場化的體制,降低發電成本,讓消費者最終受益,但機制長期不理順,最后的結果是改革無法實施下去。” 電價上調關系到百姓民生,筆者認為應該三思而后行,目前發改委價格司有關負責人表示,并沒有看到調價方案。這也說明管理層并不認為,電價上調是解決電力企業損失的有效方法。解決這一問題的提前應該是建立一個良性的行業發展機制,平衡各方利益,而不是一味的將壓力轉嫁。俗語說,家家有本難念的經!聽煤企、發電廠和電力公司三方的聲音,似乎各自為政、各有難處。細究之下,在“市場煤、計劃電”的格局下,埋頭“賺錢”的煤炭企業和高呼“賠錢”的發電廠確實遭遇了電力改革的過渡期尷尬。
正如煤企所言,“賺錢”的并不一定不合理,不能作為“讓利”的依據。由于中間環節的暴利,電廠肩負的沉重的成本負擔也并不都來自高煤價,比如鐵路運輸的價外加價、煤炭稅費的不斷加重和各地名目繁多的收費項目,最終都會轉嫁到火電企業的發電成本之中。
不過,作為寡頭陣營的電網公司掌握著電力調度交易權,備受輸配成本不透明與職工薪酬過高的非議,這卻是不爭事實。是退避三舍還是激流勇進?在由三大集團扭成的利益鎖鏈上,“棋至中盤”的電力改革正面臨抉擇。
正如煤企所言,“賺錢”的并不一定不合理,不能作為“讓利”的依據。由于中間環節的暴利,電廠肩負的沉重的成本負擔也并不都來自高煤價,比如鐵路運輸的價外加價、煤炭稅費的不斷加重和各地名目繁多的收費項目,最終都會轉嫁到火電企業的發電成本之中。
不過,作為寡頭陣營的電網公司掌握著電力調度交易權,備受輸配成本不透明與職工薪酬過高的非議,這卻是不爭事實。是退避三舍還是激流勇進?在由三大集團扭成的利益鎖鏈上,“棋至中盤”的電力改革正面臨抉擇。
 手機版|
手機版|

 二維碼|
二維碼|